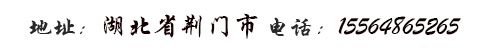故事丨血染促织经
|
当日寇铁蹄践踏中国的大地时,江南古城中一本小小的《促织经》也遭到魔手。为了保护祖国的文物不被掠夺,平民老百姓以大无畏的精神,前仆后继用鲜血保护了民族的尊严。 年初秋,秋阳如炙,余暑未消。江南名城姑苏城内的玄妙观,是全城最热闹的地方。这天下午,三点钟光景,玄妙观内三清殿后面的一小片树荫下面,三五成群地围着几个人圈子,人圈中还时不时发出此起彼伏的叫喝声。原来每当秋风乍起,蟋蟀初鸣之时,三清殿后面的这块绿荫地就约定俗成地成了斗蟋蟀的集中之处,且大多以此赌钱。因此引来不少看热闹的人。 其中东首第一个人圈子,围的人特别多,外圈的人踮着脚,伸颈向里张望着。这时双方还未正式开斗,人圈子中间置一张破旧的半桌,半桌两边站着两个斗蟋蟀者。其中一人,姓曹名天龙,30来岁,中等个子,是瀚月轩古玩店的小开。半桌的侧面站着一个谢顶的老人,即所谓的公证人,也就是裁判。在公证人的主持下,他们已经敲定了赌注的数目,只待点燃狼烟。此刻曹天龙从香云纱衣袋中取出一枚金光熠熠的带柄放大镜,手柄上还隐隐可见“御赐姑苏蟋蟀王”几个小小的篆字。 他对公证人说:“让我看看他的虫好吗?” 公证人转首瞟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曹天龙向对方微微欠了欠身子,小心翼翼地揭开对方蟋蟀盆的盖子,左手拿起蟋蟀盆,右手拿着那枚放大镜,欲凑近细察对方的蟋蟀。不料他的目光突然凝滞在人圈子外侧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身上。那人身穿一件宽大的本白色府绸长衫,鹰隼似的目光,在俯视着人圈里面的半桌。 曹天龙脸上掠过一丝紧张而又忿然的神色。他用微颤的手将蟋蟀盆盖子盖好,并把手中的那枚放大镜迅速地塞回衣袋之中。 “哦,对不起,我,我不斗了。我….”话未说完,曹天龙双手已捧起自己的那只青灰色的蟋蟀盆,拨开人丛疾步而去。 公证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和那斗蟋蟀的主人,面面相觑,大惑不解。 原来,那圈外的中年男子是个东洋人,名叫本野彦郎。本野彦郎原是日本东京东方史馆的研究员。东方史馆是以收藏和研究东方诸如朝鲜、中国、印度等国家地区文化史料、文物等为宗旨的国属机构。而本野彦郎是馆中潜心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是个中国通。 随着日军的侵华,日本政府对中国进行罪恶的文化掠夺,而本野彦郎就是负有特殊使命来到中国苏州的。为便于他开展所谓的“工作”,日军侵华总部委以他苏州宪兵副司令之职。他的任务是搜集和盗取吴地一带的文化史料和文物古籍。 他于年初来到苏州,在两三个月前的一个傍晚,他曾带领一队宪兵洗劫了瀚月轩古玩店,抢走了店中所有的文物古玩。店主曹穆钦,亦即曹天龙之父,眼看自己苦心经营的古玩铺,如今毁于一旦,怎不令他心碎欲裂。他不顾年迈,上前啐骂道:“强盗,畜生!” 暴戾的本野彦郎,恼羞成怒,嚎叫着拔出指挥刀,将曹穆钦劈死在血泊之中。当时曹天龙在一旁,本欲上前与本野彦郎拼命,但被其母死死拽住不肯放手,只能眼看着本野彦郎带着许多玉器、字画等物扬长而去。 这日本野彦郎忽然心血来潮,脱去军服,穿上中国人的服装,一副中国老百姓的打扮,独自闲逛到玄妙观,想乘机发现一些深藏在民间的文物古董。如果穿了日军军服,人们一见即避,他就难以遂愿。 当他来到三清殿后面时,只见这里围着一个个人圈子,伸颈一看,是斗蟋蟀的。他在日本从未见过斗蟋蟀,只是从史料上零星知道中国自古便有这一民间趣事。于是他十分有兴趣地挤进人圈子里张望。哪知他刚伸头向里观看,不料其中一人竟抱盆而去,不觉很是扫兴。他当然未认出曹天龙,而曹天龙却是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残杀父亲的刽子手。 本野彦郎回到宪兵司令部后,马上遣两名宪兵去将沙世堂请来。 沙世堂原是个三流评弹演员,几年前,因嗓子突然失声,声音嘶哑难听,不能说书唱曲了。于是他整天像个二流子似的东游西荡,寻机吃吃白食,打打秋风,混一天是一天。有时他也出入于赌场、青楼,因此,认识了曹天龙。当日本人来后,沙世堂就一头栽进东洋人的怀里,干起丧节辱国的勾当,成了一个众人唾骂的狗汉奸。 这天沙世堂正在家里喝茶哼曲,一听说本野彦郎请他去,立即一溜小跑着来到宪兵司令部。 “沙先生的,你的请坐的。”本野彦郎一见沙世堂就微笑着说。 沙世堂受宠若惊地躬着身子,一个劲地谄笑着说:“谢谢司令,谢谢司令。” “沙先生的,斗蟋蟀的,我的今天出去看到的,你的可知道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的?”本野彦郎盯着沙世堂说。 沙世堂没想到本野彦郎会对斗蟋蟀这种民间活动感兴趣,便讨好地说:“知道,知道。”他瞥了一眼本野彦郎,顿了顿,又说:“听老人说苏州在清朝时就出了个蟋蟀王。他的曾孙现在还活着,有60来岁了,名叫盛浩儒。当年,盛浩儒的曾祖父善于鉴、养、斗蟋蟀,同治年间,受皇帝之召进京专门在皇宫内喂养蟋蟀。由于他精心侍弄蟋蟀,让皇上观斗作乐,因此龙颜大展,御封他为姑苏蟋蟀王,并赏给他许多珍宝。据说,当年蟋蟀王从京城载誉归来后,还呕心沥血以蝇头小楷写成了一本《促织经》的书。这是一本详尽阐述蟋蟀的品种、喂养、鉴别、斗技等等环节的经典之作,非常有价值。喔,太君不知道,这促织就是蟋蟀。” “哦,《促织经》?这本书现在哪里?”本野彦郎顿时眼中射出异彩,精神也为之大振。 据说:此书代代相传,现在在盛浩儒手中。盛浩儒和他先辈一样,也精于此道,只是前几年突然丧妻,加上年岁日迈,就渐渐疏于此事了。”沙世堂喋喋不休地说着。 “沙先生的,你的快快讲,这个盛浩儒的家住在什么地方?”本野彦郎迫不及待地问。 沙世堂忙说:“不远,不远,他的家就在观前街南面的天妃巷。” “好,沙先生的,你的大大的皇军的朋友的,走,快带我去找盛浩儒的。” 本野彦郎来中国不久,就悟出像沙世堂这样肯为日本人效力的本地人对他开展工作是极为有利的,只是这种人太少太少了。 于是,本野彦郎带着四个宪兵,在沙世堂的带领下,很快来到位于观前街南面的天妃巷巷底。 盛浩儒中年才得一子,名叫盛舒庭,才20来岁,他对盛舒庭甚是宠爱。而盛舒庭也非常聪明,读书时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平时很喜欢古诗词和制谜射虎。盛舒庭在苏州东吴中学高中毕业后,由于酷爱美术,又能绘几笔丹青,就考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深造。因此,目前只有盛浩儒一人在家。 此刻盛浩儒刚洗完澡,躺在天井里的一张竹躺椅上歇息。天井很大,靠南面有一口双井。说是双井,其实是一口大井,只是有两个并列的井栏圈而已。井栏圈为青石凿就,由于年代久远,非常光滑。石圈上还留下道道绳痕。 门虚掩着,沙世堂领着本野彦郎推门而进。盛浩儒闻声起身,见是沙世堂带着几个日本人突然而至,不由有些意外。 “你的盛先生的,是吗?”本野彦郎跨上一步,超过沙世堂,双脚叉开站在盛浩儒面前。 盛浩儒未语,默然看了一眼本野彦郎,又转首看看沙世堂。 “噢,盛老先生,这位是宪兵司令本野彦郎司令。他就是盛浩儒。”沙世堂媚笑着说。 盛浩儒知道沙世堂已随为汉奸,不屑地白了他一眼,微微欠了欠身子,心中暗忖,此番沙世堂领着东洋人来此,定然没有什么好事,好在自己早有准备。 “盛先生的,别紧张的,我的是来和你交朋友的。你们中国和我们大日本的都是礼仪之邦,注重友情的,对不对?”本野彦郎笑着说。 盛浩儒对他侧目而视,仍然不发一言,心想你们到中国来杀人放火,干了多少坏事,居然还恬不知耻地讲什么友情、朋友。 见盛浩儒一直闭口不言,本野彦郎心中十分恼怒,但他依然强作笑颜地说:“盛先生的,听说你有一本《促织经》的书,我的非常感兴趣的,想借来看看的,过几天就还给你的,好不?” 盛浩儒微微一怔,到此时方知本野彦郎是冲着《促织经》而来,不由暗自庆幸,幸亏自己已将此书藏妥,否则,后果难料。 于是,盛浩儒装出一副漠然的样子说:“书?什么书?《促织经》?没听说过,没听说过。”说着,他连连摇头。 刹那间,本野彦郎收敛了笑容,眼小凶光毕露,恶狠狠地说:“你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快,把《促织经》的交出来,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的。” 盛浩儒看了看沙世堂,冷冷地对本野彦郎说:“谁对你说有这本书的,你就问谁拿好了。”说着又瞪了一眼沙世堂。 本野彦郎一怔,没想到盛浩儒会这样回答自己,竟一时语塞。 沙世堂在一旁见本野彦郎气得说不出话,忙上前一步,皮笑肉不笑地对盛浩儒说:“盛老先生,我看你还是好好想想,把书借给司令,过几天他就会还给你的,你放心好了。” 盛浩儒索性再不答话了。 本野彦郎非常恼怒地大声喝道:“搜!给我搜!” 四个宪兵闻风而动,冲进屋里,乱翻乱寻,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将盛浩儒的蟋蟀盆、网罩、水盆等喂养蟋蟀的器具弄得满地皆是,狼籍不堪,但却不见那本《促织经》的踪影。 本野彦郎沮丧地沉吟片刻之后,将沙世堂拉到天井的一旁,板着脸轻轻地问道:“沙先生的,你的话是不是真的?” 沙世堂声音微颤地说:“司令,真的,真的,绝对是真的,大家都知道的,错不了,错不了。” “嗯,走,把这老头给我带回去的!”本野彦郎立即提高了嗓门,命令着那几个宪兵。 宪兵们上前将盛浩儒扭绑着,与本野彦郎他们一起回到宪兵司令部。 一到司令部,本野彦郎就命人将盛浩儒毒打一顿。 盛浩儒虽然身上鞭痕累累,痛如椎心,但他仍然咬紧牙关,只字不吐《促织经》的藏处。本野彦郎没想到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也会如此不屈不挠。无奈之下,他只得命人先将盛浩儒关押在一间小屋子里。 夜晚,盛浩儒躺在地上,浑身剧痛难忍,四肢一阵阵抽搐着,骨头也像散了架似的。他暗忖,看来此番被抓来宪兵司令部凶多吉少,难再生还。自己身死倒是小事,只是祖传《促织经》一书被自己深藏秘处,无人知晓,自己如若真的离世而去,那《促织经》秘籍,也将永不见天日,如比,岂非要愧对列祖列宗。看来只有设法将《促织经》一书的藏处告诉儿子,才能使之继续沿传下去。可儿子现在又远在上海,这如何是好呢?思之再三,他心里渐渐有了个主意。 翌晨,本野彦郎命手下将盛浩儒押至办公室里,再一次进行逼问。这时盛浩儒已奄奄一息,路也走不动,被从小屋硬拖到本野彦郎面前。 他断断续续地对本野彦郎说:“给我纸,笔,我,想写封信,给儿子。” 本野彦郎一听,不由喜上眉梢,狡黠地笑了笑,非常客气地指着桌子说:“好的,桌上有笔墨的,你的写吧。” 盛浩儒用颤抖的手,在信纸上写下了几个字,然后将信笺慢慢地装进一只信封里,又在信封上写下“舒庭儿启”几个字。尔后,他轻轻地舒了口气,扔下笔,双手紧紧地抱住那封信,返身死死地盯住本野彦郎,眼中似要射出火来,突然便“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待他身子蠕动几下后便咽了气,那封信也随之落地。 本野彦郎迫不及待地从地上拾起那封信,从中抽出信笺,但见上面既无抬头,又无落款,只有四句短句,既不像是诗,也非词,倒有点像日本的俳句。这四句短句是这样的:上边二十,下边二十,左边二十,右边二十。 尽管本野彦郎自认为是个中国通,可是面对这四句句子,他一时也坠入云里雾中,百思不得其解。他原以为盛浩儒自知不久人世,会将《促织经》一书藏处在信中告诉其儿,没想到他竟写下这如同天书般的四句话。继而一想,或许是这四句句中隐含着某种意思,暗示《促织经》的藏处,只是自己不能窥破而已。想到这里,他立即遣人去叫沙世堂来。20分钟后,沙世堂已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本野彦郎的面前。 “本野彦郎司令,有什么事吗?盛老先生交出那书了?”他喘息未定,便急着献殷勤。 “不,没有的,这老头死了。”本野彦郎说着,将那信笺交给沙世堂。 沙世堂接过信纸,见上面写着无头无脑的四句话,一下子也给弄懵了。待本野彦郎说明原委,方知道是盛浩儒刚刚死前写下的,这才凝神琢磨起来。可是他皱眉想了许久,仍不得要领,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本野彦郎司令,这,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实在猜不出。” 本野苟郎失望地看着他,要他把信带回去再仔细想想,接着,本野彦郎在沙世堂的耳边嘀咕了一阵。沙世堂像一只哈叭狗一样,连连点头哈腰,应声而去。 原来阴险狡诈的本野彦郎想到了盛浩儒的儿子盛舒庭。他想或许能藉此信笺从盛舒庭身上找到突破口,获知《促织经》的藏处。于是,他低声关照沙世堂,密切注意盛家的情况,待盛舒庭一回苏州,立即来告知他。 除了注意盛舒庭的动向,沙世堂为了讨好本野彦郎,还拿着信笺四处求人“破译”其中的含意。他也找过曹天龙,可是,人人都摇头回绝他。他懊恼不已,感到只有等盛舒庭回来后才能有个结果了。 两天后的中午,沙世堂兴冲冲地跑到宪兵司令部,对本野彦郎说:“盛舒庭刚刚从上海回来。” “嗯,好来西,你的卖力的干活,日后大大的有赏。”本野彦郎十分高兴马上带着十来个宪兵,与沙世堂一起直奔天妃巷而去。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上海的一些学校和其他地方一样先后停课了。上海美专也于日前被迫宣布停课,学生纷纷含泪离校。盛舒庭也只能潸然离开上海,回到苏州。与他同来苏州的还有一个上海姑娘,姑娘复姓端木,名紫瑜,和盛舒庭同龄。 上海美专校长柳海硕思想开拓,极力主张教学中要借助人体模特儿。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会招来社会上的种种非议的。而端木紫瑜当时竟然不顾家庭反对和社会舆论,而愿来校当人体模特儿,这在那时候要多大的勇气。盛舒庭由于对艺术的执着和痴迷,因此对端木紫瑜非常理解,并主动与她接近,给她以信心和勇气,使她愈发心坚不渝。两人因之渐渐产生了感情,最后发展到难舍难分,誓欲结为百年之好。此次盛舒庭带端木紫瑜一起回苏州,就是为了让父亲盛浩儒见上一面,在他首肯之后,两人便择日结为夫妻。 可是万万没想到,当他回到苏州家中时,邻居就告诉他说父亲已被日本人抓去拷打致死。一时间,盛舒庭只觉天旋地转,就在他悲痛欲绝之时,忽见沙世堂带一群日本人闯了进来。 “舒庭,这是本野彦郎司令,他来看你了。”沙世堂跨向前,对盛舒庭说。 盛舒庭看着本野彦郎,恨不得冲上前去将他掐死。可是一看到他身后有那么多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盛舒庭知道自己不能冲动,那样不但于事无补,反会以卵击石,将自己的命搭上。只有先压下心头怒火,把事情搞清后,再设法报仇。 本野彦郎一进来就发现盛舒庭与其父很相像,而站在一旁的端木紫瑜那绝色佳丽更使他愣住了。他思考一下后,走到盛舒庭的面前说:“盛先生的,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好好配合,千万别像你父亲那样。” 盛舒庭一听到他提及父亲,气得牙齿咬得“格格”有声。 “盛先生的,你的看看这个,告诉我那本《促织经》的藏处,你的就可以和这位漂亮的姑娘过平安日子的。”本野彦郎说着,从沙世堂手中取过那信笺,递给盛舒庭。 盛舒庭接过信纸一看,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他们是为了要得到《促织经》而将父亲弄死的。于是他将那信纸还给本野彦郎,故装糊涂地说:“父亲的书,我怎么知道在哪里呢?再说,我从来也没见过这样一本书。”说完,他侧过头去再不说话了。 “嘿嘿,看来盛先生不想和我们大日本的好好配合,那么请吧,我一定会好好招待你们的。”说着,本野彦郎向宪兵们使了个眼色。宪兵们一拥而上将盛舒庭和端木紫瑜带回了宪兵司令部。 不管是好言相劝,重金引诱,还是严辞逼问,甚至酷刑相加,盛舒庭都不为所动,一口咬定不知有关《促织经》一书的事。 本野彦郎又不敢把盛舒庭弄死,因为他父亲死后,他就是唯一的线索了。无奈之下,他只有想别的办法来威逼盛舒庭。于是,他开始养起蟋蟀来。最近他还得到一头十分凶悍的大蟋蟀,与别人相斗,战无不胜。他想可以在那个美丽的上海姑娘身上做做文章了。他就叫人把盛舒庭押来,对他说:“盛先生的,你的是蟋蟀王的后代,我的要和你斗蟋蟀玩的,赌注就是那个花姑娘的,你输的话,她就是我的,你赢,你就可以和她一起回去。” 盛舒庭听后,心里十分奇怪,不知本野彦郎又在耍什么花招? “怎么样?你现在先回去准备准备的,明天下午三点,我在这里等你。”本野彦郎说完,叫人将盛舒庭推出宪兵司令部的大门。 盛舒庭步履沉重地回到家里,只见家中一片狼籍。他呆呆地坐着,头低垂着,十指埋在发间,心乱如麻。浓重的夜幕渐渐将他紧紧罩住,他还全然不知。 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同时有人在轻声呼唤:“舒庭,舒庭。” “谁?”他说着,开亮了灯,一看原来竟是曹天龙,惊愕之余,冷冷地问道:“你?来干什么?” 曹天龙脸上带着愧疚之色,上前说:“舒庭,虽然过去我们两家不和,可是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仇人,我父亲给他们杀了,令尊也给他们杀了。因此,我们要携起手来,一起和这帮强盗斗!” 盛舒庭被曹天龙的这一番话说得半信半疑,一时呆住了。 “我已经听说了,本野彦郎要和你斗蟋蟀,我就是为此事来的。”曹天龙说着,取出了他那枚放大镜。 盛舒庭一看,更是惊异不已,原来他们两家之仇,就是因这枚放大镜而来的。 当年同治皇帝赐给盛浩儒曾祖父许多珍异奇宝中,最为珍稀的就是一枚放大镜。这枚放大镜的圆框和手柄都由黄金制成,而且手柄上还有“御赐姑苏蟋蟀王”七个篆字。曹天龙之父曹穆钦本性贪婪,风闻此事后,日思夜想欲以重金购买此放大镜。可是,盛浩儒纵然金山银山摆在面前也不肯出卖此镜。 曹穆钦见盛浩儒不肯卖,就藉口借来欣赏几天,并写下契文,以做凭证。 盛浩儒深信不疑,想有契文在手,绝无后顾之忧。岂料心术不正的曹穆钦事先在砚台中放的是乌贼鱼肚中的汁水,用这种汁水写的字,两三天就会消失殆尽。过些时日,盛浩儒欲向曹穆钦索回放大镜时,曹穆钦竟矢口否认有此事。盛浩儒成竹在胸,取出契文一看,竟是白纸一张。就这样盛家的传家之宝被曹穆钦略施小计而得手。 后来放大镜到了曹天龙手中。因为他和别人斗蟋蟀赌钱,总是输多赢少。于是他就请人在那放大镜的手柄上做了些手脚,在里面装进一些麻醉剂,又装了一个不易察觉的暗钮。只要稍稍一按,麻醉剂就会以雾状喷射而出,不注意的话,肉眼难察。无论多么凶猛的蟋蟀被这麻醉剂一熏,就会变得软弱无力,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因此曹天龙在和别人斗蟋蟀之前,都要装模作样地用放大镜看一看别人的蟋蟀,这样必胜无疑。他也因此而赢了不少钱。 “这枚放大镜本来就是你们的,现在物归原主。”曹天龙将放大镜郑重地交给盛舒庭,并将它的奇异之处讲给盛舒庭听。 “明天上午我在家里挑一头上好的蟋蟀送来,下午你就带着蟋蟀和这枚放大镜去宪兵司令部与那日本鬼子相斗,一定赢!”曹天龙说着,微微有些激动。 “曹天龙,在这种时候,你能来帮我,我真不知该……”盛舒庭心情十分激动,不知用什么语言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别说了,舒庭,我代九泉之下的父亲向你,还有你那已经含恨死去的父亲表示歉意,请你原谅我父亲吧!” 盛舒庭更是泪如雨下,点着头,说不出话来。 次日上午,曹天龙果然送来一只青灰色的蟋蟀盆,里面放着一头翅衣黑亮的蟋蟀。 下午,盛舒庭带着蟋蟀如期赴约。他按照曹天龙所嘱而行,果然将本野彦郎的蟋蟀杀得一败涂地。本野彦郎恼羞成怒,还未等盛舒庭提出放端木紫瑜回去,竟命人将他毒打一顿,然后赶出了宪兵司令部。至此,盛舒庭才意识到自己还是太幼稚了,日本强盗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干得出来,难道他们会言而有信! 盛舒庭踉踉跄跄地回到家里,站在天井中那口双井的井栏圈前面,心中的怒火在燃烧。他紧紧地握着双拳在坚硬的石栏圈上猛力击打着,血染青石,心中的血也在泊泊地流淌。 黄昏时分,本野彦郎斗败蟋蟀后的余怒未尽,便叫人将端木紫瑜押到自己卧室,关严房门、欲对她施暴,以发泄自己的兽性。 亭亭玉立的端木紫瑜像一头孱弱的小鹿,瑟缩在一旁。 “啊,花姑娘的,来,一起来快活快活的。”本野彦郎见了惊恐中的端木紫瑜,一种兽欲般的畸形心理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满足。他淫心勃发地走向前,伸出了毛茸茸的手臂。 端木紫瑜本是个有主见的姑娘,自从知道盛舒庭之父被本野彦郎活活打死,早已对他有了刻骨的仇恨。现在他又将魔爪伸向自己,一瞬间,她已拿定主意,宁死也不受辱。她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从容而微笑地说:“别过来,我来,我来。”说着,她向床边走去。突然她将头向一旁的桌角上撞去,顿时,鲜血四溅,倒在地上。 听到端木紫瑜的死讯后,盛舒庭眼前一黑,有如五雷轰顶。他紧紧地握住拳头,咬着牙,思考着复仇的计划。 三天之后,上午八、九点钟光景,本野彦郎带着十几个宪兵气势汹汹地冲进盛舒庭家里。盛舒庭抬眼一看,不见沙世堂,嘴角不由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本野彦郎径自走到井边,转过头对站在一边的盛舒庭说:“哈哈,我的知道啦,那书的在井里,我的马上就能得到《促织经》的,哈哈。”他得意地狞笑着。 盛舒庭神情坚毅地缓缓向井边走去,在离双井两三米的地方驻足观望。这时,只见本野彦郎弯着身子,向井里张望着。 突然,盛舒庭飞快地窜上前去,将本野彦郎提起,抛向井里。本野彦郎猝不及防,未待他喊出声,“扑通”一声已掉进了井里。 宪兵们慌作一团,有几个宪兵向盛舒庭开枪,盛舒庭应声倒在井边的青石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原来,盛舒庭在极其悲恸之下,决定舍身为亲人复仇除寇。那日他从上海回来,一看到父亲写给他的四句句子,就知父亲将那本《促织经》藏在家里的井中。过去他常和父亲互相制谜猜谜。他知道父亲写的谜面:“上边二十,下边二十,左边二十,右边二十。”其谜底是“井”字,也就是暗示他书藏在井中,确实盛浩儒为防不测,早将《促织经》一书卷紧后放进一只瓶里,瓶口以蜡封严,再用油纸包好系上一块砖头,扔在井里。 盛舒庭从井底将那本《促织经》取出,连同那枚放大镜一起,存放在一个足可信赖的亲戚家。然后,他找到曹天龙,与他相商,要他假意告诉沙世堂书在井底。曹天龙觉得好是好,但在本野彦郎去盛舒庭家之前,不如先除掉沙世堂,否则可能会出意外。并说他自有办法,商量停当,两人一起在井底装上一些削尖的竹扦,尖头朝上。 然后,曹天龙假意声称有要事相告,将沙世堂拉到玄妙观旁边的黄天源点心店里。他知道沙世堂最爱吃的点心是生煎馒头,就买了好几个生煎馒头。当沙世堂去取生煎镘头时,曹天龙迅速取出随身带的一只小瓶,将放有毒药的醋倒在桌上的小碟子里。然后他若无其事地等着沙世堂来。沙世堂用筷子夹着生煎馒头,蘸着醋,吃得很香,而曹天龙向来不喜食醋,这是沙世堂知道的。 曹天龙边吃边装着不在意的样子对沙世堂说:“哎,你上次问我的事,我想了好几天,现在想出点眉目来了,上边二十,下边二十,左边二十,右边二十,这不是一个“井”字吗?怎么啦?你问这个干啥?” 骤然间,沙世堂的筷子停在空中不动了,鼓起的腮帮也停住不嚼了。他“啪”地扔下筷子,“嗖”地站起来,飞快地向宪兵司令部奔去。 “本野彦郎司令,我,我知道了,那书藏在盛家的井里,快,快去。”话刚说完,沙世堂就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双唇由紫渐黑,手足急剧抽搐,浑身痉挛不止,片刻间,便一命呜呼了。 本野彦郎闻听欣喜若狂,顾不上救沙世堂,立即带着一队宪兵,直向盛舒庭家扑去。谁知等待他的却是盛舒庭炽烈的怒火,等待他的是自取灭亡。 据说,解放之后,《促织经》一书和那枚珍异的放大镜一起归于国有。它们至今仍珍藏在南京江苏省博物馆内,供人欣赏,同时也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feihaimaz.com/dwwzfb/12600.html
- 上一篇文章: 数数诡秘之主这本现象级神作帮助乌贼创
- 下一篇文章: 故事王子不是真的爱你